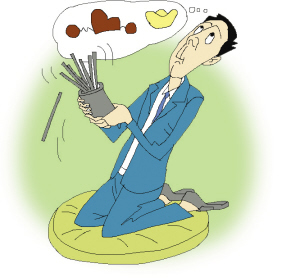|
||||||||||||||||||||||||||||||||||||
 |
|
|
2010 年 2 月 5 日 星期 五 |
|
||
| 听一听这些“中国通”的话 |
| 陈 仓 |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千年皇权专制体制导致的官僚主义流弊甚深,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官本位意识、等级观念、顺民意识,自私保守,习惯人治,迷信天命,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思维,手脑分家,散漫,缺乏公民意识。费正清指出,2000多年来,孔孟之道主导地位造成的思想惯性根深蒂固,因此,中国人热衷于琢磨人,不善于琢磨事,治学一直以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这种思维定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感情,易走极端,好赌博,重刑罚,财迷心窍,迷信鬼神,表面上傲慢自大,实际上处世谨小慎微,处人胆小怕事,遇事软弱无力。另外,中国人(小市民)很“商业性”,富于心计,聪明伶俐,投机钻营,功利,圆滑,狡诈,小商贩的商业欺诈比较普遍,但大商号比较讲信用。 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曾认为,中国人“无为”容易变为消极地服从,保守容易变为习故安常,变为恐惧及不喜变化,最严重的问题是不知个人权利为何物,蔑视个人权利。 英国伦敦来华传教士麦华陀认为,中国人逆来顺受,生命力顽强,重名誉,但中国人刑罚残酷,虐待囚犯,平心静气地用极端方式对犯人处以体罚和死刑。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认为,中国人粉饰虚伪,假意殷勤,遇事投机,奴颜婢膝,顺而不从,不求正确,有私无公,无恻隐之心,言而无信,尔虞我诈,死爱面子活受罪;中国人活易死难,耐性好但麻木,知足但保守,顽固坚持过去的风俗习惯,喜欢走老路,感觉按老规矩做事保险;中国人盲目排外,傲视外国人,不注意卫生、通风和生理学;中国知识阶层不注意多神论、泛神论与无神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对人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谛置若罔闻。 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认为,尔虞我诈的官场使身处其中的中国人老奸巨猾,利欲之念是中国人的普遍属性,讨论钱财、算计“买卖”是他们生活的最大乐趣。中国人对外国人既有好奇心,又存在极大的偏见。中国读书人动作迟钝,行动迟缓,爱面子,不务实,知足但墨守成规,重视家庭和祖先但漠视公共事务,普遍地存在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利希霍芬先后7次来中国考察,著书评说中国19省人的性格优劣,其中说到的毛病与时下的说法相近。 外国人劳德撰文指出,中国人的行为充满了矛盾,爱面子,爱排场,却不讲卫生,即使是上流社会中人,随地吐痰,随便擤鼻涕。中国人(衙役)讲仁义道德但滥施酷刑,刑讯逼供,手段残忍,官员讲礼义廉耻但贪污腐化、功利主义,迟钝,好色,软弱涣散,不守纪律。普通人幼稚又敏锐,狭隘且轻信,迷信且怀疑,敏感但缺乏科学好奇心,斤斤计较但做事不精确,经常习惯与旧习惯和经验妥协。 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散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撰文指出,中国人忍耐但善于消极抵抗,艰苦且善于享乐,多灾难但善笑,贪婪且爱面子,怯懦且缺乏同情心,骚动且平和,极端且善于调和。 20世纪初,来中国考察的法国军医勒津德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中国人创造能力薄弱,反应能力贫弱,缺乏先见之明,感觉迟钝麻木,注意力分散,缺乏肉体活动力,忽视推理能力,缺乏进取精神和科学好奇心,自负,利己,无情,报复心强,缺少抱负,迷信,无信仰,食言且伪瞒,言不由衷,顺从且没有主体意识。 日本学者大谷孝太郎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矛盾性有深刻认识,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人尊大且脆弱,亲切(对熟人)又残忍(对陌生人),轻信且怀疑,日常节俭遇事却铺张浪费,孤独却喜欢群居,拉帮结派却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利欲强且好面子,在苦恼中残喘却对之微笑,常识的、实际的想法与理想的、想象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柏杨先生对自家人的毛病归纳为:脏、乱、吵、假、大、空、嫉妒、自私、狭隘、猜忌、不团结、窝里斗、走极端、自我膨胀、消极盲从、因循守旧、不懂反省、一盘散沙、两副嘴脸、膝盖酥软、官性侵蚀人性、仁政其表暴政其里、“酱缸”文化腐蚀人心。 老外说的虽有中西方文化视角差异、信息量和个人认识局限,但我们回头看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至少说准了某些方面特征。柏杨先生的言论虽然很激烈,但也最全面。柏杨先生走了,但我们的精神疾病尚未痊愈。特别是假、大、空、多疑、嫉妒、势利、狭隘、守旧、内耗等,我们都曾切身感受其苦。虽然说历史在进步,国人也在社会发展中纠正着某些国民性格中的缺陷。但是,回看这些批评依然使人警觉,自我批评使人进步;世上无柏杨,国人当自省,树立“礼仪之邦”大国之形象。 本栏插图 玉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