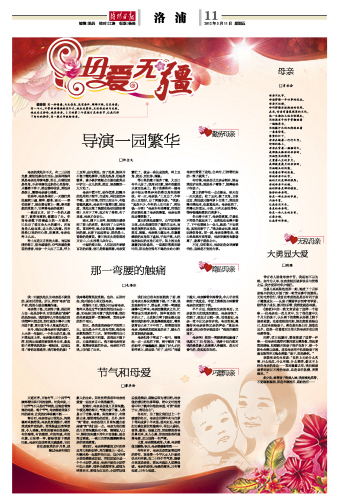|
||||||||||||||||||||
 |
|
|
2012 年 5 月 11 日 星期 五 |
|
||
| 勤劳母亲 |
| 导演一园繁华 |
| □许全义 |
母亲的菜地并不大,有二三分的光景,羞怯地躲在村西头。如果种粮种菜是母亲在导演电影,那么,庄稼地便是名角,不必导演花过多的心思指导,只需播下种子,然后静待收获,菜地却是新人,需要母亲耐心调教。 前些年,母亲身体好,一天能往菜地跑两三趟,播种、锄草、浇水……哪怕没事了,她也要去踅上一圈。事关家庭的菜篮子,它牵着母亲的魂呢! 一跌进正月,枯了一冬的大蒜醒了,被春雨滋润,都露出了头。年前母亲撒下的碾盘大的一片菠菜,已长出了猫耳朵大小的嫩叶。西南角是几畦韭菜,边上是几沟葱。用来换换口味的空心菜、油麦菜,母亲也种上几丛。 种土豆是正月里的大事。雨后放晴的春日,阳光暖暖的,空气里满是麦苗的清香,母亲一个人扛了工具,带上土豆种,走向菜地。到了地里,她却并不急于翻地播种,而是先热身,沿畦垄锄草,拿小铁铲蜻蜓点水般在菠菜丛中铲大一点儿的菜,然后,便是翻那一大片地了。 母亲不慌不忙,动作优雅,把翻开的地用耙子蹚平,打成沟,再把表面弄平整。这个时候,往往已到正午,有饭香随风飘来。母亲并不急着回家,她知道,菜地正敞了胸膛在热切地期盼着呢!只有下了种,地才有了希望、有了灵魂,母亲才会安心。 浇水,摁下土豆种,她的指尖感受到了黄土的欢悦,她听到了土豆种在笑。直到种完,她才会直起身,捶捶酸困的腰,从脚下远远望去,黄的是土,青绿的是麦苗。麦田的尽头是青黑的万安山,山头挂着几朵白云。 中原的春天短,人们还没有看够百花的烂漫,便已是春意阑珊。母亲更繁忙了,拔去一些长成的菜,种上豆角、黄瓜、西红柿、辣椒。 等田里的麦子抽齐了穗,大豆已有半人高了。我周末回家,便有香嫩的水煮豆在桌上。院子角落里有一捆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搭豆角架的树枝。有一天,母亲说:“土豆出了,今年的土豆很好,出了两编织袋。”我说:“真是不少,今年的土豆可贵了,两块钱一斤呢!”母亲本有些得意,用我们的话更怂恿了母亲的得意,母亲去菜地去得更勤了。 夏天的菜地最繁华,由平面变得立体。北头是腰间挂了穗的早玉米,南端是茂密的豆角架,还有红红绿绿的黄瓜、辣椒。母亲掰几穗玉米,在藤蔓缠绕的豆角架下盘桓,手起手落,大把温润如玉的豆角已在手。架上的豆角藤蔓仍四处悬挂,一层紫花散落在绿叶间,那豆角仿佛有不竭的生命力呢!母亲空着篮子进地,出来时,已挎着沉实的一筐子蔬菜了。 有时候,母亲会让父亲去割肉,她去菜地铲韭菜。她说孙子嘴馋了,她得给孙子包饺子。 夏日的奢华在一点点褪去,秋天在一天天逼近。收了玉米,摘了豆角,立秋过后,菜地就只能种萝卜白菜了。菜地变得开阔起来,也寂寞起来。母亲也闲了,闲得无所适从,于是,只有无奈地等待,等待窖藏经霜的白菜萝卜。 冬天终于来了,母亲很落寞,早晨也不再很早就起来了,去菜地也去得不勤了,下午也要睡上一会儿。她说:“不去菜地,真的没事干了。”我让她去玩牌,她说玩牌伤身体。那一刻,母亲显得苍老。我心里忽然有些苍凉,母亲导演的电影谢幕了,谢幕于萧条之中。 不过,明年春天,母亲还是会导演繁华的,虽然是不变的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