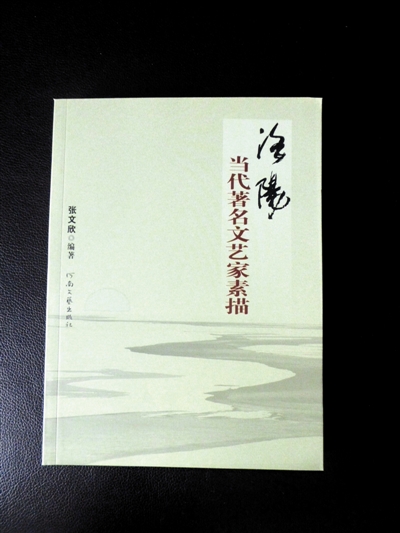|
||||||||||||||||||||
 |
|
|
2014 年 7 月 7 日 星期 一 |
|
||
| 读 家 |
2003年,连科的又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受活》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受活,是我们熟悉的豫西方言,有快乐、享乐、快活、痛快淋漓的意思,也有某种苦中作乐的味道。这部小说大量使用了豫西方言,并在每一章节后面都用絮言的形式对这些方言进行注释。 《受活》的故事仍发生在阎连科特有的那个现实和荒诞交织的耙耧山脉,一个全是残疾人的受活庄演绎着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人间悲喜剧——残疾人组成的“绝艺团”的巡回表演,县长柳莺雀要去俄罗斯买回列宁遗体的狂想式的宏伟计划——这些情节都使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受到挑战。 《受活》又一次在文坛掀起一股旋风。据不完全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有20多篇评论文章在各种报刊发表。当然,有赞誉,也有批评和论争。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在没人推荐的情况下偶然读了《受活》,慨然著文,他说:“读后真让我拍案叫绝,激动不已。不写下一点阅读心得,简直无法平静下来。”在深刻分析了作品的情节和精神特点外,他最后强调:“其结构、语言、叙述方式又全都是独创的。所以,我要认真地说,中国出了一部奇小说。” 《受活》当年在全国小说排行榜上位居榜首。后来它又先后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鼎钧双年文学奖。在著名媒体《南方周末》举办的“新文学三十年10部优秀文学作品”评选中,《受活》以高票入围。这本书还相继被翻译成日、韩、英、德多种文字,在日本、韩国、英国、德国出版。 2004年,阎连科从解放军二炮电视剧艺术中心转业,到北京市作家协会,当了一名专业作家。北京作协群星灿烂,有一批全国著名的作家,如张洁、刘恒、邹静之等。大家都非常热情友好地欢迎连科的到来。 但是,他不久后发表的一个小长篇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创作基本形成了两年至三年一部的周期。有关部门对他的批评,并没有影响他的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并没有对他的个人生活,特别是文学写作造成任何影响。 在这期间,他写了长篇小说《丁庄梦》。 《丁庄梦》是写艾滋病的,这是一个敏感的题材,也是一个痛苦的题材。为了写这部书,他曾经多次跑到艾滋病泛滥成灾的豫东某地的一个村庄,采访,体验。连科在以前自己几部小说中,写卖皮卖肉这种人生的惨烈,写苦难、写死亡,但多是虚构。可这一次眼前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事实:这里的农民为了生存或所谓致富,去大量卖血而导致了艾滋病传播肆虐,接着是大批死亡。直面苦难和死亡的写作,使连科一直处于痛苦之中。 阎连科在题为《写作的崩溃》的《丁庄梦》后记中,详细记述了他在写完这部长篇小说后那种“内心无所依附的苦痛和绝望”的感觉。
毛泽东每天接触的各界人物,对于那时的国民来说,只能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却难见其面的。 从上午9时到晚饭后,本来是《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采访毛泽东,结果几近角色对换,大都是毛泽东采访记者了。 毛泽东首先询问重庆新闻界的情况,记者说他对上层人物很少接触,对中下层的公教人员了解较多。毛泽东详细询问这些人的生活、思想、情绪,他们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对国共谈判的看法。记者尽其所能,把听到看到和自己的切身体会都谈了。毛泽东说,死跟蒋介石的人只是少数,有的人不满现状,但对美蒋还有幻想,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毛泽东对赵超构说,如果没有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运兵运枪炮,大片的沦陷区是会由人民收复的,因为“八路军就在城门口”。 在这个世界上,美国的影响无处不在,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毛泽东自然关注。也巧了,有三个美军士兵主动找上门来。 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和杰克·埃德尔曼,在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总部工作,来华已经一年半多了,先后到过昆明、上海,不久前调来重庆。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知道敌后根据地军民抢救遇难美军飞行员,知道延安的中国是另一个样子,但只是听说。来到重庆,听说这儿就有共产党的“小解放区”,红岩村13号和曾家岩50号,就想去那里见识见识。他们结识了一些中国朋友,其中包括曾在西南联大做地下工作的李拙文,通过他联系,约定去红岩村的时间和暗号。 三个士兵准备了一堆问题,结果像那位记者赵超构一样,几乎颠倒了个儿。 月初,毛泽东还会见了两个美国青年,韩丁和格里·坦纳鲍姆。前者曾经从事农业,搞过农业工会,后者有过工人和组织工会的经历。毛泽东向他们了解美国工人、农民的生活,工会的组织和斗争情况及其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农业局和农场主联合会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大多数工人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来,杜鲁门对工人、农民采取什么政策。 记者赵超构说毛泽东“慈祥和蔼的态度和生动的谈话,能使一个最拘谨的人解除顾虑,把自己心里话倾倒出来”。贝尔则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对我们极为坦率,对我们的访问表示高兴——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快”。“个性非同凡响,第一次见面就给人深刻的印象,使你不由自主地喜欢他”。 “八一五”后的蒋介石,无论表面上怎样如日中天,自觉稳坐钓鱼台,都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了那个时代。 |
|
≡ 洛阳社区最新图片 ≡ | ≡ 百姓呼声 ≡ | ≡ 洛阳社区热帖 ≡ | |
≡ 聚焦河洛 ≡≡ 亲子教育 ≡ | ≡ 公益慈善 ≡≡ 房产家居 ≡≡ 汽车时代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