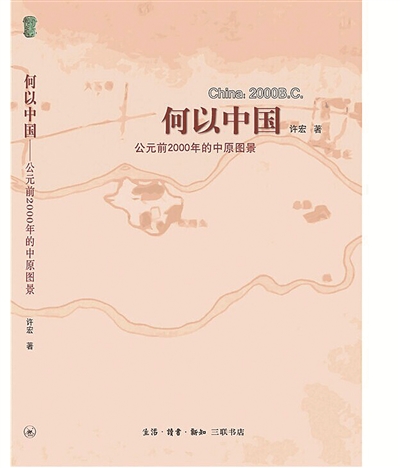在中国历史上,城址林立的时代一般也是群雄竞起、战乱频仍的时代,如龙山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而大凡存在有国势较强的广域王权国家或帝国、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设防都城的比例也相对减少,如夏、商、西周三代和秦汉时代。可以说,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给数百年来中原地区城邑林立的争斗史画上了一个句号。新砦是战乱状态的终结者。
比较一下新砦与既往龙山城邑的聚落形态,差异立现。首先,在大河以南的中原腹地,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还是首次登场。其次,它抛却了方正的城垣规制,而以并不规则的壕沟连通自然河道、冲沟,形成防御体系。这种传统的中断是迫于政治军事形势,还是因人群的更替而显现出更质朴务实的思想,抑或折射的是由“大同”向“小康”过渡的社会结构转换的进程,引人遐思。
无独有偶,“新砦类遗存”的另一处重要聚落——巩义花地嘴,也有内外两重(四条)环壕,与伊洛河及其支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这类多重防御设施划分出的多重空间,一般被解读为同一聚落内不同安全等级的空间区域,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社会成员很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等级地位,聚落内部的分化较为明显,当然也有可能不同壕沟之间为聚落不同性质的功能区划。
前已述及新砦大邑的主要防御设施是壕沟。其中中壕内缘的若干地点还发现了宽10米左右的带状夯土遗存,发掘者推定为城墙。但从夯土全部位于沟内、远远低于当时的地面、夯层多向外倾斜的情况看,这应是为防止壕沟壁坍塌所实施的加固处理措施。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新砦遗址有高出地面的城墙存在。就现有的材料看,当时的新砦遗址应是一处大型环壕聚落。
内壕以内发现的所谓“大型建筑”,实际上是一处长条形的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活动面低于当时的地面,发掘者直呼其为“浅坑”。这个大浅坑近东西向,现存长度近百米,宽10余米。浅坑内垫土和踩踏面呈“千层饼”状,只是在南北两壁上发现有加固修整的迹象。“大型建筑”的南侧地面上发现有整猪骨架和埋有兽骨的灰坑,此外还有若干柱洞,或与附属建筑有关。
类似的浅穴式遗迹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的祭祀遗存区也曾被发现,只是规模没有这么大。两处遗址的发掘者都推测这类建筑很可能就是《礼记》《尚书》等书中所载“墠”或“坎”之类的祭祀活动场所。
新砦聚落的发掘与研究才刚刚起步,像古城寨和二里头那样高出地面、显现政治威势的大型宫室类夯土建筑尚未发现,已揭露的新砦浅穴式建筑并不是这一系统中的链条之一,不属同类项。因此,认为其“面积比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的殿堂还要大,很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并据此推测“新砦城址很可能就是夏启之居所在地”的观点,还缺乏考古学材料的支持。而“新砦期”的大冲沟“不禁使人联想到传说中大禹治水历史背景”的推想,恐怕也只限于联想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