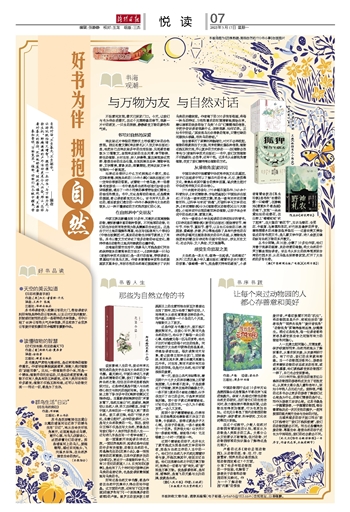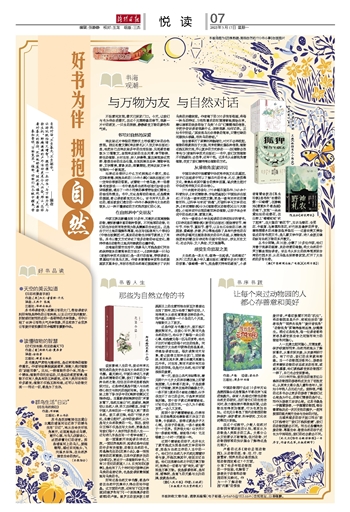说到影响人生的书,我近年来比较沉迷的是关乎生态与大自然的文学书籍。毫无疑问,中国古诗词几乎就是自然博物的汇集,我们了解的每一种自然之物,往往在古诗词里都能找到对应。这些诗词真是中国人与自然倾心相交与相托的深刻写照。我从书架上取下珍存多年的《陶渊明集》《王维诗选》。当重新读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我感到,陶渊明以自然入诗,终又在诗歌里,存留下中国人共有的另一个更恒久更广袤的自然。我又读王维,他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幼年的我读时,以为是写大自然极美的一句。现在,我明白王维不仅是在写大自然,更像是在写我们每个人曲折而多思的人生——这句诗几乎是在写一个哲学命题了。
我一面重新开启阅读古诗词之旅,一面狂热地购买、阅读近些年出版的许多有关植物、动物及自然的书。郑逸梅先生的《花果小品》,像一张张清淡的花草素描;日本作家柳宗民的《杂草记》,更近于一本植物科学书;又有20世纪的英国人J.A.贝克写的《游隼》,是他用了几十年时间对游隼这种鸟类的追踪记录,也是我读到最细腻地写鸟类的书。
所有这些自然文学书籍,都是作者在自然中沉浸许久得出的写作结晶。这方面的代表,还有写下《瓦尔登湖》的梭罗和写下《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卢梭。梭罗主动放弃波士顿蒸蒸日上的生意而独自到瓦尔登湖边生活了两年,因为他想了解并证明,人活得更为从容究竟需要怎样的条件。而卢梭,在隐居一个小岛的几个月里,与植物交上了朋友。
这些作家与书籍之外,我不能不提到契诃夫。在我心目中,契诃夫是自然的知己,他似乎了解每一朵云的心事,他能看见每一匹马的哀愁,他也不忘打听路过的每个村庄的消息。同时他把于大自然中获得的那些真谛,传递给读者如我。每次读契诃夫写景,都让我想立即冲出家门,回到森林、草原及流水旁,看云朵看月亮看马匹牛羊。对生活,契诃夫或许有无法抹去的悲观,但是对大自然,他只怀着深深的爱意。
有一天,我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看见两个六七岁大的男孩蹲在地上盯着地面看,几分钟都不起身。于是我凑近了仔细看,原来在地砖的缝隙之中,一条不到3厘米的小蜈蚣在蠕动,似乎决定不了自己的去向,于是来来回回地折腾。两个孩子就这样看着蜈蚣,讨论它会去的方向,一会儿为小蜈蚣发笑,一会儿又发愁。
那两个孩子蹲着看蜈蚣,仿佛车站、目的地等其他事物都不存在了的场景,令我感动。我想这就是赤子之心啊。在孩子的眼里,一条小蜈蚣等于一个世界。世界很大吗?似乎并不如一条蜈蚣有趣。蜈蚣很小吗?它足够看上一小时一天甚至一年。
这两个看蜈蚣的孩子,也许长大了就可能成为那些自然文学的写作者,那些为自然立传的人当中的一个。他们对大自然几乎天然充满着好奇与爱,并能沉浸其中,彻底忘记自我。他们在观看自然之中的万事万物时,觉得这一切都与“我”有关,或“我”即是万事万物。我是婆婆纳草,是河流、蜡梅树,是南飞的天鹅与北归的雁,我就是自然。
(据《人民日报》 作者:王晓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