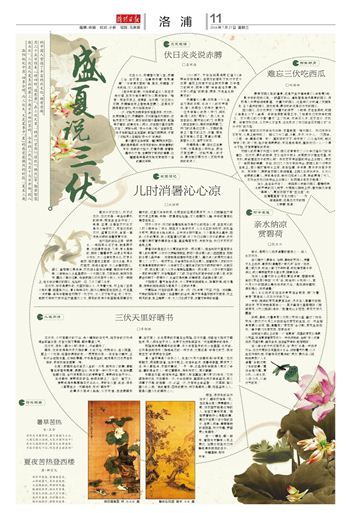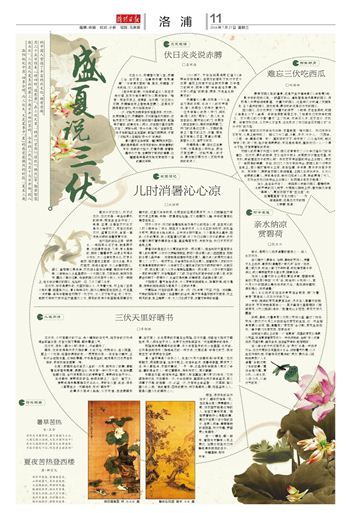三伏天,乡村有晒伏的习俗,选个晴朗的好天气,将家中的衣物被褥全部拿出来,放在太阳下暴晒,晒去霉湿之气。
三伏天,读书人晒什么呢?读书人,只能晒书了。
晒书,我总觉得是件很风雅的事。长日风轻,绿荫深浅,在小院里,搭上一个板架,将屋中满架的书,一摞摞抱出来,一本本渐次铺开,让书沐浴在阳光里。这样的暴晒,于书是有益的,就像是我们沉浸在书海中,感觉到自在惬意一样。
也有人把晒书当成自己人生的一次秀,就秀出了故事。清朝著名学者朱彝尊,满腹经纶。传说有一年六月六日,他袒胸露肚晒太阳,恰巧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看见。康熙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晒书。康熙感到奇怪,就和他聊上了。经过一番交谈,康熙觉得朱彝尊确实才华出众,便封他为官。此后,读书人都要在这一天晒诗书,形成“晒书节”。
此事多少有点儿蹊跷,似不可信。但袒腹晒书事,古已有之。比他更早的东晋名士郝隆,三伏天里,仰卧在太阳底下晒肚皮,别人问他在干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在晒腹中的诗书。”
郝隆和朱彝尊晒书的故事,多少总有些秀的成分在里面。也可能,这只是旧时读书人推销自己的一种方法,大概还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想在作怪吧。
清人潘平隽是个好书之人,他在《六月六日晒书诗》中写道:“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如游千载上,与结半生缘。读喜年非耋,题惊岁又迁。呼儿勤检点,家世只青毡。”一岁一年,这些诗书伴随诗人度过了半生,喜的是全家人一起忙着晒书,诗书传家久,其乐融融。
书晒在外面,就难免被盗。桐城人张祖翼在《清代野记》中说:“文渊阁每年伏日,例日晒书一次,十余日而毕。直阁学士并不亲自监视,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晒一次,必盗一次。亦有学士自盗者……究其弊,皆以国为私之病。”由此看来,图书的散佚,并不是晒书之罪,那些盗书之人,都是以国为私的晒书之人。
现在,保存书的条件好多了,晒书恐难得一见,但还是会有人羡慕晒书之趣,作家陆苏就是这样的人。她在文章中写道:“每每想着就开心得醉的事,莫过于在某个好太阳的日子,在燕儿筑巢、青藤掩映的庭院里,布衣布鞋、素面素心地晒书。”
选一个晴日,晒一回书,看阳光安静地从书上拂过,如拂过那些我们安静地捧书而读的日子。
书籍温暖,时光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