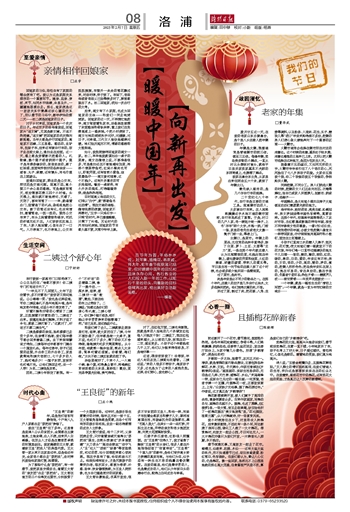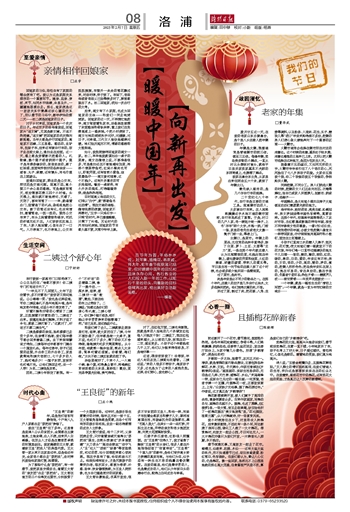腊月廿五这一天,在我的老家山东乐陵奎台,是十里八乡庄稼人赶年集的日子。
年集是大集,规模通常是普通集市的两三倍,甚至三五倍。每逢年集,卖各类货物的小摊点,一直从村北头摆到村南头,就连平日里买家卖家基本不光顾的东西街道上,也摆满了摊点。
我家在奎台东北角,从家里出来往西走五六十米,就到了年集北口。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几个存自行车的招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距离集市远的人,大多骑自行车来。在人流熙熙攘攘近乎水泄不通的集市面前,自行车显然成了累赘。于是,村口的几户人家,寻一硬纸片做一牌子,上书“存车”两个大字,木棍一挑,门前一竖,家里的老先生或老太太搬一凳子门前一坐,等客上门。
北集口,是菜市。年集上的菜品,比往常的品种丰富得多,除了白菜、萝卜、土豆、大葱等“主力”菜,一些在那个年代被庄稼人认为比较精细的菜,也能出现在年集上,诸如碧绿的芹菜和韭菜、火红的辣椒、娇嫩的蒜黄、带刺儿的黄瓜等。平日里生活一向节俭的庄稼人到了这个时候,也会或多或少地买回一些精细菜。
过了菜市,是肉市。
肉是年货里必不可少的物品之一。在那个年代,庄稼人的肚子里几乎没什么油水,大多选择买肥肉。他们觉得太瘦的肉,不香。
买过了菜,割过了肉,把花椒、八角、生姜等调料,以及粉条、人造肉、花生、瓜子、糖块儿等“进口”年货采购得差不多后,赶集的男人们便心急火燎地奔向下一个重要的区域——火鞭市。
火鞭市通常会选择在集市所在村庄的池塘边。这个时候的池塘,基本处于枯水期,池塘边潮湿的土地早已上冻。之所以把火鞭市选择在这种地方,是因为怕发生火灾。
既像看不见的磁石,又如同无形的大手,火鞭市牢牢吸引住了八十老汉的心,死死拴住了七八岁男孩子的腿。大家你五挂我十挂,你二十块钱的我五十块钱的,争相购买火鞭。
同样赶集,不同分工。男人们挑选火鞭的时候,赶集的女人们正走向布匹、衣帽等摊位,给自己或家人买围脖儿、扯新布、挑袜子、选鞋子……
年画摊点,是大姑娘小媳妇及婶子大娘甚至奶奶们最愿意光顾的地方。
连年有余、招财进宝、虎虎生威、松鹤延年、男女胖娃娃等年画色彩鲜艳,寓意吉祥。在那个年代,明星照年画渐渐进入了农村市场,当红歌星或影星的特写年画,深受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喜爱。一番讨价还价后,一张张卷好的年画,会被女性赶集人像宝贝一样带回家里,仔仔细细地用高粱秆和小铁钉,固定在土坯墙壁上。
令孩子们直流口水的糖人儿馃子、纸风车、花灯笼,使大姑娘们看一眼就放不下的花衣服,叫爷们喝一口直呼过瘾痛快的地瓜干儿白酒……香的,辣的,酸的,甜的,红的,绿的,黑的,白的,黄的,年货应有尽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赶集人形形色色;把各类年货扛在肩上的,抱在怀里的,背在身后的,提在手里的,负重者千姿百态;热包子喽——糖葫芦儿哎——甜甘蔗喽——叫卖声此起彼伏……
一个年集,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一个年集,就是一首为年而忙碌的交响乐……